《上大学》-小说-毕琼
上大学
引子
咱就是个卑微人,样貌也一般般,还是个矬子,一两白酒落肚,话就多起来,我听人说咱都是长平街道上的人,算老乡了。
算。
他笑眯眯的,把半截褂子搭在肩膀上,裸露着一身腱子肉的臂膀。
再喝一杯,加深加深感情,我添了二十串羊肉串,他摆摆手,不喝了。
串热热的上来了,不喝,就吃串。
要不?喝点啤酒,这个酒劲小。
对方摆摆手,不喝。
不喝,咋聊?
我这个人酒量也不大,喝酒喝到一定份上,肚子里的话才开始往外掏,酒意也就微微的上了额头;我闭上眼睛的片刻,串子下去一多半,一杯酒下去了三分之一,我没有惊讶,现在禁酒令下达后,我这爱让酒的毛病改了。能喝多少就喝多少,尽量别催酒让酒。
尤其坐在眼前的这个老老乡。
我醒来的刹那间,他站起来就走,改日我请你吃饭喝酒,你急什么,再聊一会儿。
你不知道我就是一两酒的量,一天两回喝,中午一杯,晚上一杯,啥也不耽误。
日日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
有人劝他,多喝一杯晕乎乎的多舒服,现成的酒肴;我跟你不一样,你夜里渴了喝水,有人伺候你,我呢?
你,你怎么啦?
我,我单着。
单着?你有退休金,当老师的,八千多呢?怎么不找一个呢?
我找过,找过五回,都不长久,图钱。
不找了,找伤心了,咱上了岁数,不想那个事了,喂,你是考学考出来的么?
不,咱以前是民办老师,后来转出来的。
转出来的,那个矬子又补充了一句,咱是村里的,教了一辈子。
你贵姓?
我姓马。
我说,马老师,你跟四中的刘老师熟识么?
他比我大。
只能说认识。
俺俩一块考出去的,文革后第一批,在县上我的考的分数在头几名里。
我心里犯起嘀咕,你老马自己说是由民办转的公办,是不是民办转公办,考试成绩靠前,你真会张冠李戴;一两多酒就开始信口开河了。
也许人老了,老糊涂了。
他似乎也看出了我的疑惑,不解释,离开饭桌,来到公园的假山周遭布放的石凳上小坐。
我想起了我的一个同学,跟马老师在一个小学学校里当老师,马老师说,我知道。
我那个同学反馈给我的信息是真有那么一回事,不说谎。
问为什么考上没去,那可是改变命运的机会,就白白的放弃了。
别提啦?
我也是听别人议论的,问过他,他支支吾吾的不肯说,好像有什么难言之隐。
哎,事情过去了很多年,一经提起,马老师一点遗憾也没有在脸上表露。
那件事情在十里八乡都引起了轰动。
说什么的都有。
马老师奔八的人了,好汉不提当年勇,摇摇头不说了,不说了,口气里夹杂着无奈的语气。
同时那挥舞的手势像秋风吹落的树叶,飘飘忽忽的落下来,机械似的落下来,一点也不连贯。
我瞅瞅离去的背影,低下头,我们隔着不远,几乎每天都能相见。
到了晚上。
一
兄弟,我让你瞧瞧,瞧什么?
不告诉你,让你瞧了你不就知道了么?
稍等一会儿,一会儿就等不及了,接着就是一声唏嘘的口气,我屏住气息,会是什么稀罕文物?
什么呀,搞的这么神秘?我心里直嘀咕,这马老头给我搞什么名堂?
先是打开油漆的木盒,木盒不大,打开红布包裹的一层,又揭开薄薄的一层,才露出那个庐山的真面目,录取通知书。
名字有些漫漶不清楚,前面的那个马字还是清晰的映入眼帘;是山大录取通知书。
我看一眼心里就跟着震撼一回。
马老师小心翼翼的将宝贝放进木盒里,木盒盛放在铁箱子里面,我们是在家家悦的超市里一个僻静的角落看的。
超市里凉快,外面不保险,黏糊糊的汗液粘附在上头说不定就会给沾染上不洁的东西。
你让我看到底啥意思?
我让你看看这东西,告诉你我不是说谎,你别在你的小说里把我给写歪了。
你怎么知道我写东西。
我听别人说的,不是一个人,我从你的眼神里看到你当时的表情,是什么样的表情,我觉着有必要让你知道真相,知道我不是胡说一气。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上学去?那是多么好的机会,一个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怎么会放弃,即便是天大的困难不能克服一下么?
马老师面对我连珠炮似的追问,不急也不恼,我把它放回去后,回来给你说,你等等我。
我说我在这里等你,等着。
他摆摆手。抱着铁箱子蹒跚的离开,上了三轮车,嘟嘟的开走。
我没带手机,就没法子看时间,等了接近一个钟头,我估摸着,见他还没出来,是不是在地摊上等我,超市夜里九点打烊,我走出超市,迎面就是一股热浪扑面。
老马这是唱的哪一出?
说好的一块见个面,答应一块坐坐,吃个饭,说是回请,也许儿子孙子不让出来,或是来了客人,比如闺女女婿来了,一时走不开。
我怏怏不快的往回走,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他怎么啦?
我一晚上都没睡好,梦里梦外都是他,笑呵呵的看着我,莫非驾鹤西去了。
到早晨醒来的时候,人还在梦里醉着。
这个老头的笑容可鞠的来到眼前晃荡,把我都给晃荡晕了,淅淅沥沥的雨丝发出啪啪的拍打地面的声音、拍打玻璃窗子的声音,树叶子随风摇曳的声音像风铃摇醒了我的梦,梦里的沉醉也被风给熏染成哀怨的曲调。
要知道老马就这么离开,我不让他打开他那个宝贝该有多好,遗憾扔出去,扔到我的头上,碰的一声,挥挥手;那个年代考上没有不去的道理,天底下的人谁不惋惜,惋惜后,会带着另一种思索想,是不是真的,至于说的困难完全都是托词。
谁家没困难,说的冠冕堂皇,跟真的一样,谁信呀?老马为什么打开让我瞧稀罕,都多少年过去的事了,可见在老马的心灵里残留着些许的遗憾。
让我瞧就是弥补那份遗憾,就是让我的笔墨别把他仅有的一点骄傲的资本给抹杀掉。
等到雨停风止,更闷热的湿气裹挟着来到地面上,来到大地的上空、各个角落里弥漫那滚滚的暑气,树上的叶子绿油油的,茂密成一小片林子,被树干擎举成一把伞,稳稳的一动不动。
风丝也不来,那个让我惦念的老马也没露面,在他接送孩子的路上也没碰见。
我一连等了三天,我估计老马出状况了,问他一个小区的人,除了摇头就是一头雾水。
好奇心促使我一探究竟,我找到物业公司打听,业主不是那个人,也许你找的那个人离开这儿了,搬到别的地方去了吧。
或是回老家了,你是什么关系?
我没回答物业人员的问题,一个人往回走,走到公司大厅里面,巨幅草书吸引了我的目光。
大厅里出出进进的人从我身旁走过,一点也没惊动我,手在空中比划起来。
华灯初上,保安过来给我打招呼,我这才从草书的氛围里挣扎出来,对保安笑笑,看来你对书法有研究,研究谈不上,只是自己喜欢,喜欢看着玩。
保安说,我看你不是嘴上说的喜欢那么简单,喜欢多少年了,少儿时候就喜欢了,现在头发白了半个头了。你估估。
那人惊讶的叫一声,吓我一跳,难不成我肉眼看巨幅草书给看没了一截。
老兄,这么说你也是个闲人,到了耳顺年了吧。
一个耳顺把我给问懵了,我的眼睛还在巨幅的横幅草书里没移开呢?
那个保安熟悉老马头,给老马头介绍过一个老伴,提起老马头,我的心思才回转到眼前来。
刚刚开了一个头,手机电话响起来,我喂了一声,电话给挂了,想接着聊,电话重又不合时宜的想起来,“回来!”
二
老马头人间蒸发了八个多月,我也渐渐淡忘了老马头的那些往事,一句老马的话你从北山上说,你得去南山上听,你不知道他说的那一句话是真,那一句话是假。
你还听他说,保安的话让我觉着有点跑火车,你跟他熟。
当然是熟了,不是一般的熟。
一个村的?
不是。
俺们以前在肉类市场上合伙干过买卖,分开后,业务上也有交集。
他不是当老师么?怎么跟你做起买卖来了。
他当老师不假,是小学老师,利用一早一晚的搞。当镇上的肉类市场搞起来的时候,他就进来了。
他几个孩子?
三个。两个闺女,一个儿子。
考上大学的事你知道么?
我想想,应该有这么一回事,当时我才二十冒头呢?
为什么没上?
还不是困难么?
能说说么?
保安说,我还真知道一点,关键是你自己去不去,别强调过多的客观理由,你说他后悔么?
后悔肯定后悔,世上没有卖后悔药的。
保安看看表,我得走,换班的人来了,不给你啦了,我挥挥手。
一个午后,我站在十字路口处的左侧等红绿灯,一辆小轿车停在面前,摇下车窗玻璃,冲我摆手。
喂,一声喂,我发现车子里的他,他径直走过来,拽着我上了车。
到我那里瞅瞅,我想下去,嘴上说,还去么?改天去行不行?
好不容易逮住你,你这个人挺敏感,躲躲闪闪的,你老同学还能害你?
我领你接接地气。
一溜烟工夫就到了他那一亩三分地。
老张领着我看了看自己教书的那个地方,一个学生也没有了,眼神里出现了恍惚,脚步放缓,对我说起了老冯,我心里疑惑,那人不是姓马么?
难道那个老头对我撒了谎,也许重名呢?“你怎么还怀疑我说的话,就姓冯,冯庄子上的,这个小学就在这个庄子上。”
“个头不高,胖墩墩的,圆盘子脸,看上去敦厚朴实的人,说话慢吞吞的。”接着老同学找出手机里存的照片,是不是这个人?
我点点头。
他没给你说实话,留了一手?
留了一手,怎么你还不相信呀,照片都给你看了,是不是你以为我给你说的不是实话,你信他还是信我?
当然是信你了。
我就纳闷,给我卖这个关子有鸟用?我除了疑惑意外还有点讨厌的意思,我脸上的表情还是淡淡的什么也看不出来,随口说,也许年纪大了,说话颠三倒四的不怪他。
咱能不能不提他,我烦他。
我心里就是咯噔一下子,我与老张好长时间不联系了,就是因为这个所谓的马老师的事又接上了头;同学突然变脸,变的有些突兀,心里说,这个老张是小孩的脸说变就变。
想归想,何必触碰那个霉头,这里面肯定有什么不愉快的过节梗在那儿。
我看到丰盛的饭菜,瞅瞅老同学与我推杯换盏,很快就有了酒意,浓浓的写在脸颊上;我说我不能再喝了,我的酒量小,“你在我这里喝不多,也没啥好酒招待你,别见外。”
我喝着喝着就把自己给喝的睡着了,呼呼的。
我心里迷瞪着,反正我是坐着你的车子来的,你看着办,大不了就住你这里。
“你怎么搞的,怎么把人家给喝高了,你送人家去,待一会儿,反正不能在这里过夜,大热的天多不方便。”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知鸟在枝头上嗡嗡成一团,用同样的音调编织成没有节奏的旋律,我枕着这样的旋律沉醉起来。
醒来的我揉揉惺忪的眼睛,老张将泡好的茶茗递给我一盏,品品?
喂,我刚才为什么怼你烦那个老冯,说起来我与那个老冯是老亲戚,我婶子就是他妹妹。
他妹妹与老冯关系相处的不那么融洽,都不怎么来往,老人一走,这门亲事就算断了。
来家串门的就是他妹妹。
当年轰动效应的莫过于他放弃上大学的那桩事了。
说说看,这个老冯为什么放弃?
老同学反问我,你为什么对这个事那么感兴趣呢?莫非你打破砂锅问到底的老毛病又犯了。
可不是么?
他没有接着搭讪我,突然抛出一个重磅炸弹,他儿子在十四岁那年,替父亲报仇,杀了人。
三
他的这个话让我惊讶的说不出话,混沌过来的我问,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
真的,我逛你这个干什么?
是在考上大学之前还是之后发生的?
别忘了他是头一年恢复高考的时候考上的,儿子才多大,才会跑呢?
跟儿子闹出的那个大动静没关系,假设上了大学的话,也许儿子发生的那一出就不会发生。
他当时没上大学,家里确实有困难,你说谁家没困难,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他是老生儿子,出生的时候,他父亲四十冒头了。
父母年纪大了,妻子体弱,干不了重活,膝下还有三个娃娃,说是走不开也是事实。
自己拍拍屁股离开,家里咋整?可是家里纵有千般困难也不是拒绝上大学的理由啊。
可是他拒绝了,白白地丢掉上大学的一个名额。
他安稳的教着书,当孩子王。
幸好赶上了好政策,从民办教师转成了公办教师,他没一心扑在教书上,抽时间干个买卖,挣个外快,贴补家里。
因为生意上的事,难免不得罪人,儿子失手打死了人,被判了十年徒刑。
老冯经过这个打击,家里积攒的那点家底彻底折腾光了,还欠了饥荒。
怎么办?
好在这时候转成公办教师了,收入有了保障;日子才慢慢的缓过劲来。
在自己的村里教了一辈子书,心思都在琢磨怎么挣钱上,儿子还在里头,出来后会是啥样子?
以后的花销肯定是个天文数字,现在人们都向钱看了,不多弄点钱怎么翻身。
时不时的请同事撮一顿,大家不怎么攀比,一个老教师了,儿子还在里头。
奇怪,老冯利用闲暇时间干买卖,在村里阻力少了,外村也几乎没有了。
按照说,人家会更加看不起他,更应该欺负他,理由再明白不过了,你儿子都折进去了,你还能啥?
老冯也知道自己还教着书,不能太放肆了,自己可不敢破罐子破摔。
儿子的事直接要了老冯父亲的命。
自己要是当年咬咬牙上大学去,儿子也不会因为自己吃亏,失手打死人家。
你说我为什么知道的那么多,我告诉你,他妹妹就是我婶子,何况我还在他村里当老师,跟他是同事。
他年龄也渐渐大了,他的课也少了,学校学生也渐渐的稀少,没过几年,他就提前内退了,当时有政策。
内退的他激发出了活力,女儿们也大了,嫁人的嫁人,谁也不敢小瞧他了。
坐牢的儿子好像是一道无形的光环罩在人们的心里,别招惹老冯头。
他儿子快从牢里出来了,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老冯呢?也学着宽宏大度起来,生意场上无父子,他是有脑子的人,把一肚子的学问用在了生意上。
镇上的肉类批发市场开业了,老冯头一头扎进去了,第三年,老冯头的宝贝儿子获释,跟着自己干。
等于间接的帮了儿子一把,儿子是为了老子给人打的架,蹲的大狱。
也算间接的害了儿子。
担心儿子在外头瞎混,走歪了路。
四
儿子跟着姐姐姐夫干,后来自己单干,老冯头看到紧猪血的活计很红火,一个南方来的南蛮子有一手绝艺,就是紧猪血。
几乎承接了市场上所有的紧猪血生意,别人忙活一晚上也就紧几头猪的猪血,累个臭死。
可是那个南蛮子一晚上就紧猪血六七千斤。把整个市场都包圆了,还绰绰有余。
市场的人开始挤兑那个南蛮子。
一晃就是一年光景,老冯头跟南蛮子套近乎,很是投缘,南蛮子的手法别人学不来。
比如多少斤两的猪放多少盐是有比例限制的,是粗盐还是细盐,这个都有讲究。
虽然说,看看就会,没啥手艺,可是你干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你接了猪血,接的过程也有讲究,公猪母猪也有说法,接下来还得紧,成了块状后你还得切割,切割后放到大锅里煮。
接跟紧也是一环扣一环,马虎不得。
大火多长时间,中火多长时间,还有温火,都是有讲究的。
光放猪血不行,还得掺水,掺多少也有讲究。
南蛮子说,老冯呀,我也知道你想学,我也不打算在这儿干了,到俺那边去,我教你可以,绝活一般是不外传的。老冯明白,拜师的事人家不干,肯定谈不拢。
你开个价。
痛快。
我这就离开这里了,也没啥顾忌了,别玩那些虚的,你给我买辆新摩托车,放我跟前,我手把手教你。
买什么牌子的呢?
买雅马哈的?
老冯头心里咯噔一下子,行,我答应你。
俩女儿说他,爹,你花一万多就为了学那个手艺值不当的。
值当的。
老冯头语气坚定,儿子听说了没吭声,当初自己创业,跟老爸借钱,老爸都没开口答应。
老冯头果真买了辆雅马哈大摩托车。
跟着学了三天,看着老冯头上道了,那个南蛮子打点行装,骑上摩托车一溜烟离开了。
老冯头知道技术就是钞票,背后人都在议论值不值,当茶余饭后的谈资传播。
嘿,你上学不交学费么?你拜师找门路也不是两个肩膀扛着个嘴白让你捡便宜的。
当别人紧猪血接猪血一个晚上弄个三五百斤就算破天荒了,老冯头却一个晚上整五千斤。
干的还很轻松呢?
一时间猪血王的外号扣在老冯头身上,别的地方冷冷清清,他这地方门庭若市,挤破了脑袋。
老冯头在南蛮子基础上,又大胆的进行了技术改进,一半猪血一半清水,紧好后,外观滑溜好看,吃起来不涩,还有嚼头。
有的人买去后,当猪血买当羊血卖。
老冯头靠这个绝技发了大财,老冯头摒弃过去传男不传女的陋习;你们过去跟着我没少受罪吃苦,这个手艺渐渐的传播开来。
一个外地后生想学这门手艺,也听说了老冯头当年拿一万多元的钱换来的手艺,出资五千。
五千就五千吧,心里说,你就是一分钱没有,看你心诚的份上,我也教你;自己不收钱,对方反而觉着是敷衍人。
老冯头趁手里有几个钱,在城里买了楼。
儿子出狱后年龄就不小了,一直到做生意上了路,走上了正轨,自己才慢慢的放手。
两个女儿资产也过了千万元,日子过的那叫一个红火。
喂,你说老冯头放弃了上大学的机会,却在社会这个大学里硬生生的补上了这一课。
老天爷给你关上一扇窗户的同时,也为你打开了另一扇窗户。
五
我离开老同学的家,脑子里萦绕着他的影子,嘿,你八个月没见他,我前几天还见了他,好几套房子,不租,轮流住。
他不接送孙子上学么?
接。
频繁地给孙子换学校。
你知道么?他老婆离开后,频频的找老婆,找了五个都离开了他。
他说,女人都图惜你钱。
咱过日子过惯了,女人变着花样的给你要钱,开口还不是小数目。
就是积攒的有些,也架不住给你要,过上个一年半载的就走人。
他说的时候眼睛里的迷茫被泪花花濡染成树枝头上的花朵随风摇曳成一波波的涛浪。
拍打着你的岸头。
你还是怕花钱。
老冯头说,我怕,说出来能吓你一溜跟头,我怕,我才不怕,不过我想过来了,男的女的就那么一回事。喝个小酒,别喝多了,蛮好的。
一个跟老冯头年龄相仿佛的老人戏谑地说,是不是整花活整不了啦?人家才离开你。
嘿,咱没你那样的艳福,娶了一个可人的小老婆,日子正滋润着呢?
你别在矮人面前说,你显摆啥?
孩子们还给你那么铁么?
有一天我遇见了老冯头,我大声的喊了一声,在东风水库的公园里见着了。
我还该你一顿饭钱呢?
得回请你,不好意思,一晃就是一年的光景。
你到底怎么啦?
我出了趟远门。
我表哥找了一个对象,一个很漂亮的女人,年龄相差两岁,俩人偷偷结婚了,表侄子找到我让我去,表哥也让我去,那口气似乎是我要不去就非整出人命。
我一走就是小半年,想给你招呼一声,也没你的联系方式。
表哥被女人迷住了,工资上交,啥活都干,颌面蒸馒头,包饺子,烙油饼,累的大汗淋漓的,倍儿高兴。
表哥是吃退休工资的,工资六千多,不算低。
俩人过了小半年,那个女的是企业下岗的,也有工资,相对是要低一些。
让我劝劝表哥,我呀,是八两对半斤。
表哥住院,孩子们找出老人的卡,一查,一百块钱都不到。
问急了,就说花了。
表哥还是没保住自己的婚姻,向儿女们妥协了。
我一回来,没好意思给儿子说,怎么说呢?说不出口啊。
我九千多的工资,给我留下三千多一点,剩余的都给掠走了。
这三千多还是我跟孙子一个月的生活费,孙子十岁多一点,什么都管给我要。
弄的我捉襟见肘。不得不省着花。
哎,你应该还有个老底。
嘘嘘,当心隔墙有耳,路上说话草缝里听,这个道理你不懂?
2025年9月19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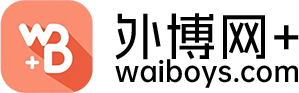











 鄂公网安备42018502008200号
鄂公网安备42018502008200号